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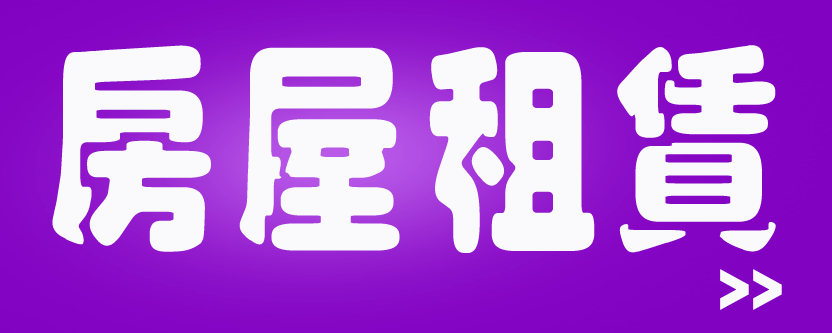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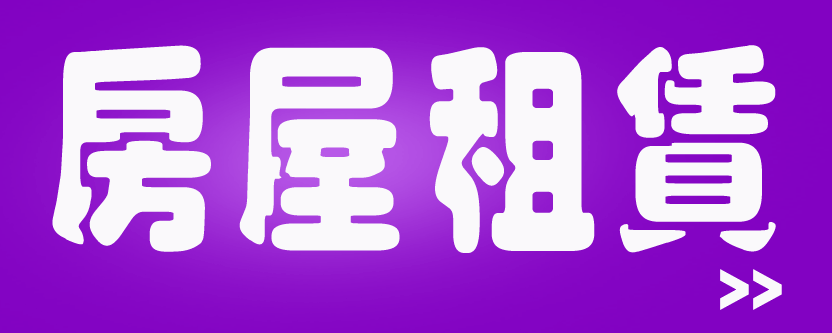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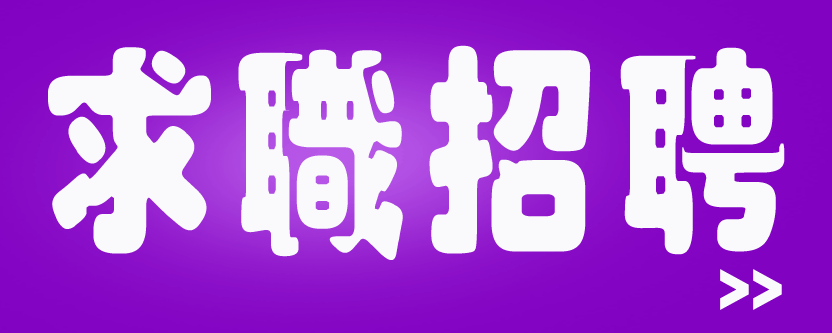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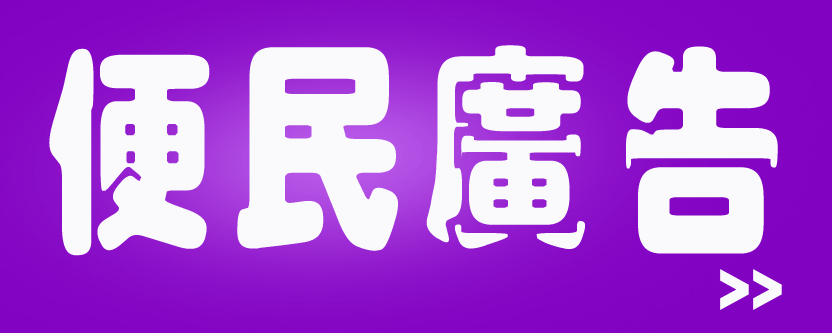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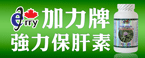
|

|

|

|

|

|

|

|

|
|
卡城新闻 加国新闻 即时新闻 娱乐八卦
最新科技 读者文摘 养生保健 美食饮品
居家生活 移民茶馆 艺术中心 风筝专辑 房屋租赁 求职招聘 便民广告 定居指南 城市介绍 房产动态 留学移民 华人故事 教育话题 财经信息 精华旅游 难得一笑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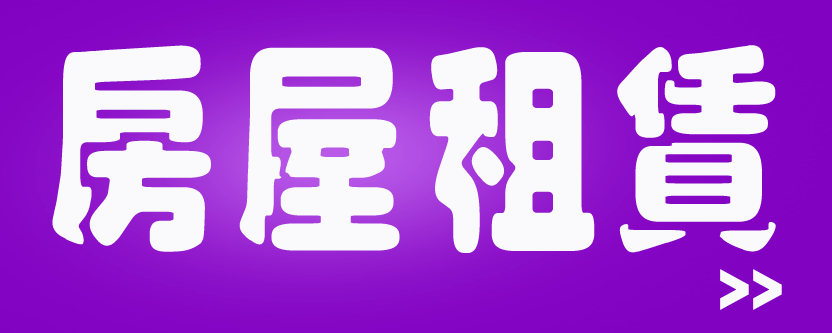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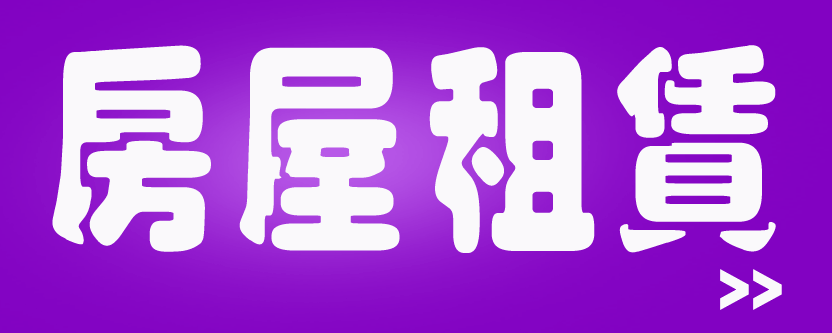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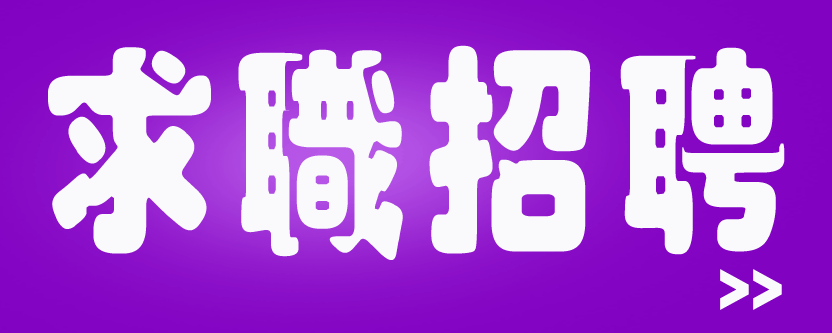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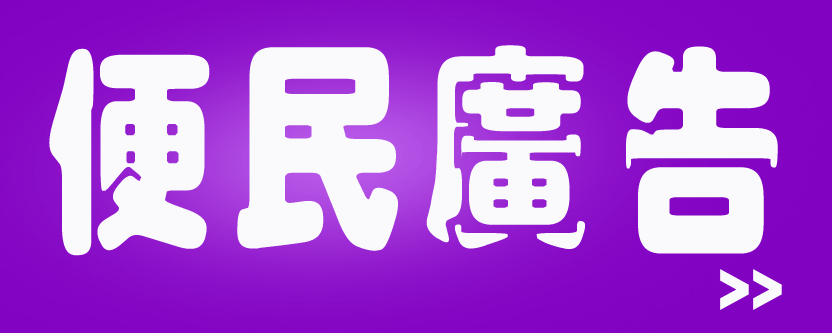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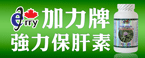
|

|

|

|

|

|

|

|

|
|
卡城新闻 加国新闻 即时新闻 娱乐八卦
最新科技 读者文摘 养生保健 美食饮品
居家生活 移民茶馆 艺术中心 风筝专辑 房屋租赁 求职招聘 便民广告 定居指南 城市介绍 房产动态 留学移民 华人故事 教育话题 财经信息 精华旅游 难得一笑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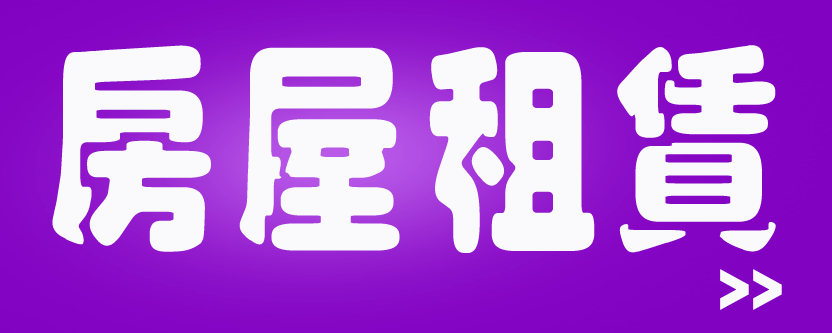
|

|

|
|
卡城新闻 加国新闻 即时新闻 娱乐八卦 最新科技 读者文摘 养生保健 美食饮品 居家生活 移民茶馆 艺术中心 风筝专辑 房屋租赁 求职招聘 便民广告 定居指南 城市介绍 房产动态 留学移民 华人故事 教育话题 财经信息 精华旅游 难得一笑 |
| 艺术中心 |
 卡城华人网信息中心 卡城华人网信息中心  艺术中心 艺术中心
  希腊悲剧《波斯人》,是巅峰或解脱? 希腊悲剧《波斯人》,是巅峰或解脱?
|
|
【卡城华人网 www.calgarychina.ca】 2025-07-21 09:42 免责声明: 本消息未经核实,不代表网站的立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
几年来,阿维尼翁艺术节都会邀请导演格温纳埃尔·莫兰(Gwenaël Morin)创作一部演出作品,作为戏剧节“拆除城墙,完成桥梁”项目的一部分。在之前的演出中,导演曾与阿维尼翁地区的业余演员们见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来协助他创作戏剧。这次也一样,导演用了四个演员来演绎希腊悲剧《波斯人》。这是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于公元前472年创作的历史题材悲剧,为现存唯一以现实事件(萨拉米斯海战)为背景的古希腊戏剧。 
格温纳埃尔·莫兰(Gwenaël Morin)导演的希腊悲剧"波斯人"剧照 ©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 《波斯人》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所有人都焦急地等待着薛西斯远征希腊的消息。一位信使抵达,宣布波斯军队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战败,众多将领战死沙场,薛西斯还活着,且正在归途中。王后前往她已故丈夫大流士墓前召唤他的影子。听到战败的消息后,大流士谴责儿子薛西斯的傲慢,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他进攻希腊。大流士的影子在消失之前预言了另一场失败——普拉提亚之战。 演出是露天的,地点是阿维尼翁艺术节创办人Jean Vilar故居花园里。四个演员穿着现代服装,在绝对极简风的舞台上通过河水般滔滔不绝的台词演绎,道具仅有一支竖笛和一个小鼓,以及地上划着的两个互相交错的白色圆圈。 温纳埃尔·莫兰接受本台专访时,话题就从这两个圆圈的意涵开始。 莫兰: 我其实开始只画了第一个圆圈,白天时我觉得它在花园里的位置很合适,但到了晚上,感觉它中间的位置好像稍微往右移了一点,于是又画了一个更适合夜视的圆圈,位置也稍微移动了一点——所以这纯粹是技术上的调整。第二天,当我听到台词时,我决定保留这两个圆圈。这个剧中确实讨论的是公元前470年波斯人组织的对希腊的入侵,有两条入侵道路,这是两条道路的具体化。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共鸣,否则就太插曲化了了。但我把这种同时存在两条道路的想法,也就是双圆的概念,叠加在管弦乐队的原理上,或者无论如何我们继承的管弦乐队的样式也是圆形的。在古典文化中,管弦乐队据说是古希腊剧院中,舞蹈者与乐器演奏者所占的位于观众和舞台之间的半圆形,或者也可以说古代唱诗班的空间实践首先基于圆形运动,是相互矛盾的圆形运动上。所以,这是一种将两者叠加的方式。令人惊讶的是,它引发了许多共鸣。 但具体来说,两个圆的交汇也产生了一种形状,它并非椭圆形,我不认为它是椭圆形。两个圆的交汇一定有个名字,也许是一个,不,是四个椭圆形。简而言之,总有一个形状接近眼睛的形状。当我们认识到眼睛的重要性时,它就位于中心。在希腊文化中,眼睛的象征意义也是如此。它是一只没有瞳孔的眼睛。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制造了,也激发了一种振动,一种视觉调节的原则。此外,还有我们自身的圆和另一个他者的圆,将两者叠加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叠加产生的振动,显然使得与他者的相遇变得无限激动人心,因为永远没有完美的契合。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扰动,新事物的发明有可能以此为基础。 法广:为什么选择这部希腊悲剧? 你说过你抵抗新实时闻的影响,但这个作品却与新闻事件有所吻合 …… 莫兰:我抵抗新闻时事。我的天职就是抵抗。但波斯人在 2600 年前占领这里纯属偶然吗?是的,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伊朗发生的事。这是历史,是巧合,是一个不幸的巧合。 事实上,老实说,我当时在做另一个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行下去。于是,在绝望中,我求助于阿维尼翁戏剧节,求助于戏剧节的总监蒂亚戈(注:Tiago Rodrigues),他就推荐了《波斯人》。 所以显然我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剧。我想,‘好吧,为什么是这部呢’?但当你请别人下订单时,你没有资格说‘听着,这个不合适’。所以,让人下订单本身就是一种默认的接受,除非出现任何争议:而我感兴趣的正是这个原因。 我试图理解他为什么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最终,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境地,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种局面,即试图理解蒂亚戈为什么邀请我上演这部戏,我没有答案。他自己可能做不到,但无论如何,我发现自己并非在肯定个人的愿望,而是在困惑地表达他人的愿望,在我看来,这似乎与今年戏剧节的“受邀语言” ,也就是阿拉伯语的问题产生了共鸣。 通过引入一种语言,无论是阿拉伯语还是其他语言,我们会陷入引入他者的困惑?事实上,问题是,我们怎么会成为自己,不是那个肯定的人,而是我们渴望的人?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文本的奇妙之处在于,就像伟大的古典文本一样,我们总是觉得它们与我们息息相关,仅仅因为我们自己……艺术的强大之处在于,我一直认为艺术是符号组织所能想象到的最完美的顶峰,因此也是意义的顶峰。然而,我发现恰恰相反,艺术是我们最终得以安息的地方,让我们从这种人类疾病中解脱出来,这种疾病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为万物赋予意义。在某个时刻,面对一件完成的作品,我们被创造意义的需要所抚慰。我们疯了,我们或许像疯子一样。我的意思是,我们几乎疯了! 因此,当我们面对像埃斯库罗斯这样的杰作时,人性的弊病再次占据了我们,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其意义,并感叹:“哦,这位埃斯库罗斯真是才华横溢!2500年前,他就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我们,面对这部作品的奇特之处,却忍不住将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战争——融入其中。”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当今的两大核心问题是:再次出现的人类彻底毁灭,以及我们称之为原子弹所带来的人类彻底毁灭,它再次以假设的形式出现,然后还有民主问题。人类,以及人类议会如何治理自己?原子弹、民主和彻底毁灭。以及他人声音的问题。如何治理?这是所有希腊悲剧的核心。这些问题在剧中引起了共鸣。在时事中发生,也在剧中上演。 法广:这出戏赋予了失败者发言的舞台......在中国传统中也说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失败者一般都没有舞台 莫兰:战败者从不发言,因为胜利者是王。不给战败者发言的机会, 战败者永远没有发言权。任何让战败者发言的人都是骗子,换句话说,他利用自己的权力说自己没有权力。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有权力的人有权力说自己没有权力。被征服者永远没有发言权,而把发言权让给被征服者的胜利者则是自命不凡。被征服者没有发言权。要发言,你必须是胜利者。你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发言。我能跟你说话,是因为每一秒我都是胜利者——我战胜了自己的存在,因为我有足够的呼吸,除了我需要的呼吸之外,我还能让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这具躯体充满活力想你讲述一些事情。说话就是胜利。因此,让被征服者发出声音,也许就是有效地让人们听到...... 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停止夺取胜利,停止征服,停止从那些被征服的人身上汲取力量。这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谈论战败者,而是让我们停止对他们做什么。让我们停止谈论战败者。 为战败者发声,已经是在传道了。事实上,我对这种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很有意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自以为有权决定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事实上,我不认为希腊人会这么做。我认为埃斯库罗斯没有为失败者发声。这种想法有点像基督教的投射,一种虚构。同情心的虚构是基督教的产物,我们对这种宏大的意识形态怀有敬意。我认为,恰恰相反,埃斯库罗斯通过向希腊人解释,这种骄傲会反过来攻击他们,就像它攻击波斯人一样,从而抬高了希腊人的骄傲。我们今天自以为征服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事实上,塑造失败者就是做自己……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尝试运用言语进行解释,但效果不佳。我得重读柏拉图了…… 法广:舞台布景和道具的简洁与观众收到的海量文字台词形成鲜明对比。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语言文字还有意义吗? 莫兰:是的,很奇怪。文字,以及我们交流的文字,其迷人之处在于,为了真正地相互交流,我们必须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分离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了彼此,必须有人倾听。而事实上,为了有人能够说话,就必须有人保持沉默。 所以,虽然语言的使命是创造意义,连接彼此,使彼此产生共同点。也就是说,存在着这种张力和模糊性,这样我才能与你对话,才能通过语言与你连接,但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一种距离关系。所以,这种张力是相对的,而且始终存在。它从来都不是确定的,事实上,即使有时某些意识形态会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与我保持距离。但这层面纱,这种距离都是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 语言在存在之间建立的隔离是一种不可接受的隔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彼此无话可说的那一刻起,就从未停止过有话可说,因为这种隔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堵墙,或者变成了一段爱情故事的终结,一个终结,或者一个结局。 你看到了语言的悖论。所以语言仍然有意义,永远有意义。只要我们能够彼此保持距离,既然我们谈论的是分离,那就可能会有些悲剧。但这种言语距离的原始悲剧是如何成为我们必须共同创造的关系的条件的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对我来说无限有用,而且语言显然能够传达意义。 法广:即使有 30 年的舞台导演经验,你还害怕观众的反应吗?你在导演过程中会考虑观众的感受吗? 莫兰:回答是肯定也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当我导演一场演出时,我从不是为了人而表演。我希望这场演出能带来一些东西,创造出观众。我不会自问,人们期待什么?我能给他们什么?我就像对待孩子一样。我的意思是,你不会揣测未出生孩子的脸。然后,在某个时刻,他们出生了,然后他们有了这张脸,这个身体,这个性别。 你必须创造一个与之相配的世界。所以,当我准备一场演出时,某种程度上,观众实际上还没有诞生。所以,他们可能脾气暴躁,可能盲目,我不知道…… 如果他必须忍受我的表演,而我显然会非常不高兴。不,有些东西是强加的 ,就像我说的语言和语法一样,但在这里,我们共享同一种语言,有一种强加的语法, 强加的词汇 ,强加的节奏 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接受一定数量的条件,这样我们的分离才会成为沃土。 法广:你会背台词吗? 莫兰:不,我不会。但因为我不想知道,我感兴趣的是在演员表演那天第一次听到它。事实上,我想成为台词的陌生人,我想成为这部剧的陌生人。我想从未见过它。事实上,我并不是带着我想象中的东西来到剧院舞台,并希望它变成现实。我是完全盲目、纯真地登上戏剧舞台的。事实上,我要求埃斯库罗斯创造一个我未曾想象过的世界。作为导演,我只是一个组织者。 我先组织演员和合作者的聚会,然后我与阿维尼翁戏剧节合作,将这个聚会扩展到公众,阿维尼翁戏剧节与公众关系十分密切。但我最多也就是个组织者而已。所以我要求演员们自己去体验,去第一次聆听它。 我希望这个“第一次”每次都能重现,每个晚上都能重现。我并不是每晚都去看演出。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死亡的古老恐惧。我不知道。观众的存在让我逃避。我不知道。我害怕被批评。我害怕等观众到了,我怕他们会一齐站起来把我吞噬掉!…… 《波斯人》这部悲剧创作于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埃斯库罗斯曾参与其中)胜利之后。虽然这些军事上的失败并未真正影响波斯帝国,但公元前480年在希腊人看来,却是一个弱小但自由的民族战胜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甚至可以说,是希腊世界战胜“蛮族”的胜利。毫无疑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幅图景似乎被简化了:某些希腊民族与波斯帝国签订了条约,而波斯帝国并非野蛮;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持续不断。然而,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骄傲,因其城邦所发挥的作用而高傲不已,并在那里找到了一种热情的素材,而诗歌正是能够将这种热情放大。 编辑(Edit) 删除(Delete) |

|

|

|
| 版权所有(C), 2002-2026, 卡城华人网中国版 www.calgarychina.ca |
| 版权所有(C), 2002-2026, 卡城华人网中国版 www.calgarychina.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