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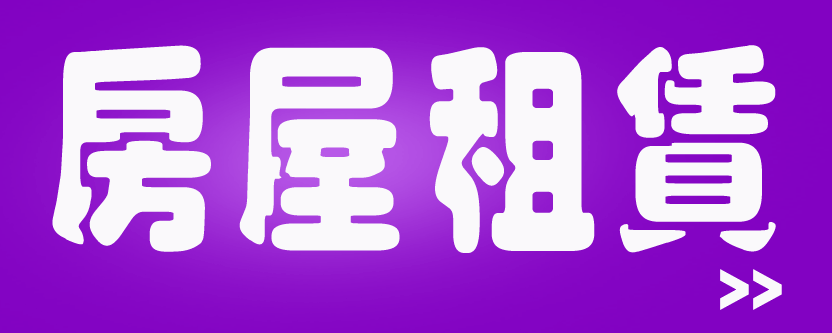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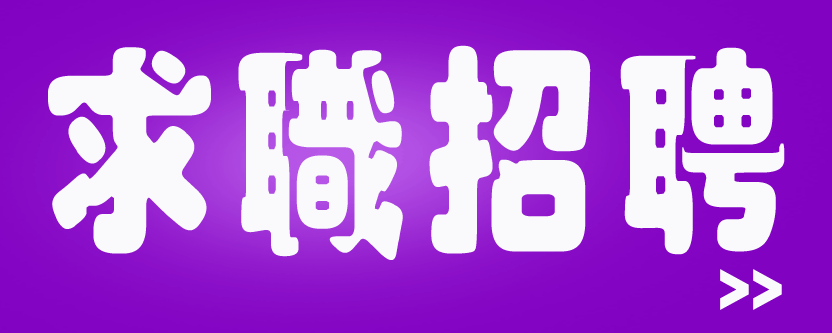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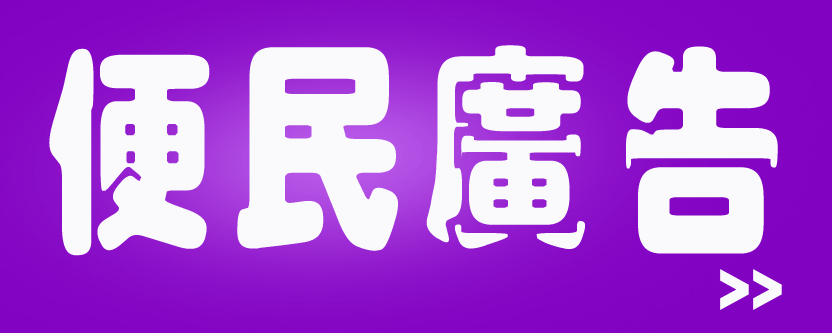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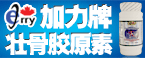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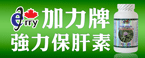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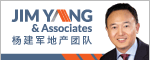
|

|
|
卡城新闻 加国新闻 即时新闻 娱乐八卦
最新科技 读者文摘 养生保健 美食饮品
居家生活 音乐诗画 艺术中心 风筝专辑 房屋租赁 求职招聘 便民广告 定居指南 城市介绍 房产动态 留学移民 华人故事 教育话题 财经信息 精华旅游 难得一笑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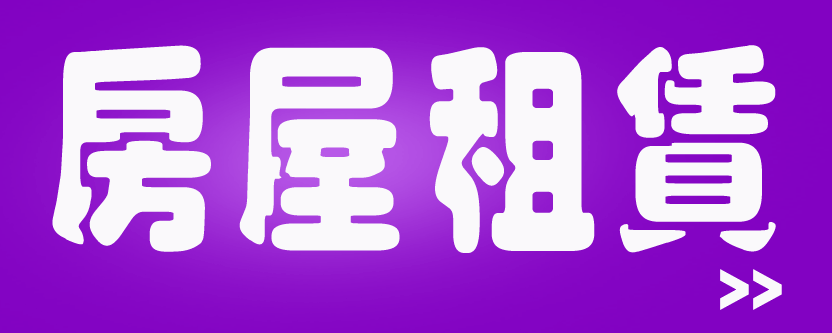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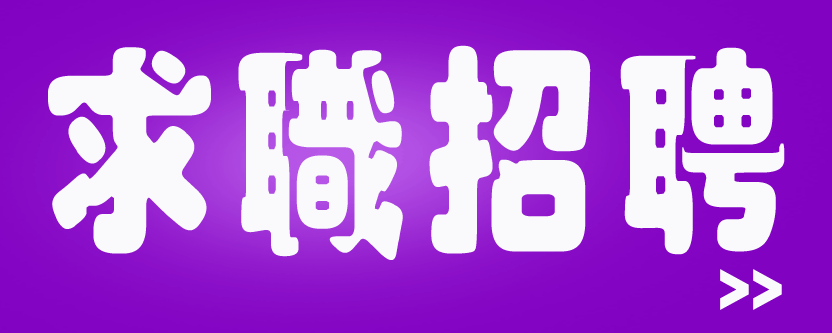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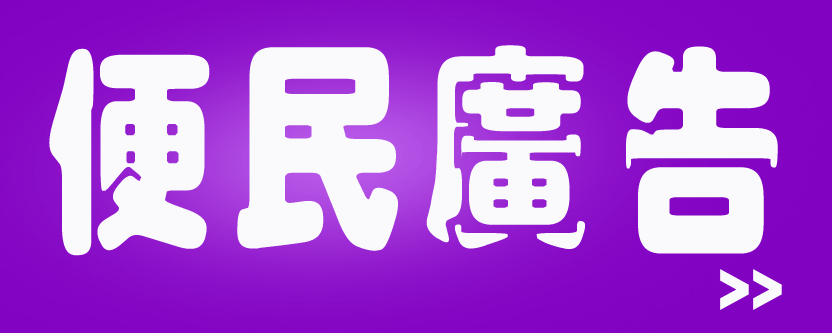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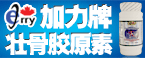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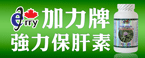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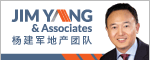
|

|
|
卡城新闻 加国新闻 即时新闻 娱乐八卦
最新科技 读者文摘 养生保健 美食饮品
居家生活 音乐诗画 艺术中心 风筝专辑 房屋租赁 求职招聘 便民广告 定居指南 城市介绍 房产动态 留学移民 华人故事 教育话题 财经信息 精华旅游 难得一笑 |

|

|

|

|

|

|

|

|

|

|

|

|

|
|
卡城新闻 加国新闻 即时新闻 娱乐八卦 最新科技 读者文摘 养生保健 美食饮品 居家生活 音乐诗画 艺术中心 风筝专辑 房屋租赁 求职招聘 便民广告 定居指南 城市介绍 房产动态 留学移民 华人故事 教育话题 财经信息 精华旅游 难得一笑 |
| 读者文摘 |
 卡城华人网信息中心 卡城华人网信息中心  读者文摘 读者文摘
  为什么路边很少见到女性流浪者? 为什么路边很少见到女性流浪者?
|
|
【卡城华人网 www.calgarychina.ca】 2025-07-27 11:41 免责声明: 本消息未经核实,不代表网站的立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
说起流浪者,我们最常想到的是中老年男性形象,这一印象也与全球多地的数据统计相吻合,在大量流浪者中,女性占比远低于男性。 然而不成比例的是,女性其实更容易陷入贫困。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全球贫困人口中女性比例普遍高于男性,尤其在极端贫困(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群体中,女性占比更高。那么,为什么在流浪者中女性反而比男性少? 这一现状引起了日本社会学者丸山里美的关注。2010年,她曾以“为什么女性流浪者这么少”为题提交博士论文(2013年以《无家可归的女性》为题正式出版)。她在后记中感慨,在数据明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的今天,那些虽然贫困却没有成为流浪者的女性到底在哪里?她们又是如何生活的? 贫困发生机制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容易成为“隐性流浪者” 2000年初,当丸山里美开始关注女性流浪者这个群体时,首先引起她的困惑的是,为什么相较于日本,其他发达国家如北美和欧洲的女性流浪者相对比例更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社会集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新流浪者”的人群,他们大多处于20-30岁,且其中女性流浪者的增长占到了整个群体增长量的三成。很多没有固定居所的人可能会根据当天具体情况留宿在熟人家里;或是网咖、廉价民宿或24小时营业的商店中。这一类女性的比例比纯粹“露宿街头”要高。也就是说,在无固定处所的人群中,女性实际上更倾向于采取露宿街头之外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了“隐性流浪者”。这一方面与女性流浪者在实际露宿中可能面临的性别暴力有关,另一方面折射出很多贫困女性被家庭所缚而“无法变成流浪者”。 在丸山里美随后为该书增补的文章《贫困女性在哪里》中,她提到了多名50多岁女性的案例。在有婚史的女性中,有8.6%的人反映遭受过“经济型家庭暴力”,也就是说女性会因为家庭内部金钱分配的不平等而无法离开家庭,这一现状在底层社会的家庭中尤其常见,正如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及日本女性贫困的社会学家琼·阿克辛所形容的那样:“她们甚至走不到贫困的女性化这一步,因为她们根本不可能离婚和经济独立。” 对于那些没有进入婚姻或已经结束婚姻的“无家”女性而言,她们大多也许获得了各种意义上的社会救济而没有出现在街头,但这种救济通常维持的也是一种伴随着耻辱感的低水准生活。丸山里美在书中提到很多看似中立的社会政策本身就存在性别差异。“因为国家期待男性从事雇佣劳动,所以即使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劳动,也会更容易申请到社会保险;而女性因为总是承担再生产劳动或者相对低薪的工作,当她们需要生活保障时,更容易与社会福利绑定。”这些福利发放规则通常伴随着对女性私德的层层审视,即便部分“无家”女性接受福利而没有流落街头,但长远来看也很难彻底摆脱贫困。 女性流浪者的生活世界:不同于男性流浪者的被排斥轨迹 由于女性更容易成为“隐性流浪者”,这群人的生活现状长期处于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之外。实际上,相比于男性流浪者而言,女性流浪者遭遇着不同的被排斥轨迹,以开始流浪的原因为例,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男性流浪者中没有婚史的占半数以上;而在丸山里美接触到的女性流浪者中,接近九成都有过婚史,其中甚至半数以上有过不止一段婚姻。这意味着想要弄明白这些女性为何走到流浪这一步,不仅要关注她们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关注她们的家庭关系。 这点在丸山里美随后的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在高度危险的露宿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些女性流浪者会选择只在夜晚睡在某位男性流浪者身旁。据日本都市生活会2000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每15名女性流浪者中有11人与男性同住,其中既有和男性伴侣一起露宿的情况,也有与在露宿中邂逅的男性同居的情况。不少单身女性流浪者称,在这样一个男性居多的街头环境中,女性想要独自露宿是相当困难的。 丸山里美曾询问多位女性流浪者,她们在公园露宿时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几乎每一位都会最先回答:半夜去厕所是最可怕的。陌生人靠近自己的生活空间本身给女性流浪者造成的恐惧是更大的。这一观察在女性杂志《美丽佳人》2022年发布的一篇调查报道中也得到了类似的反馈,街头潜在的性别暴力对女性太不友善,“她们几乎都有被性骚扰过的经验,比方说偷摸,或是言语上吃豆腐,这种情形非常普遍。除了把自己弄得脏脏臭臭,再来就是剃平头、打扮得很阳刚,要不然就是找一个比较有权势的异性来依附,大概不出这三种。” 除此之外,洗澡、上厕所等日常生理需求也存在诸多不便。男性流浪者可能会在公园等地直接裸体用水龙头的水冲洗,但女性流浪者没钱去澡堂时,就只能在公共厕所洗头。也有女性流浪者提到洗衣服也很困难,她们感觉在男性多的地方无法晾晒女性内衣(如内衣被偷等经历),只能用毛巾盖住,或者选择在不引人注目的树荫下晾晒。“这些具体问题都让女性流浪者长期处于高度紧绷和焦虑的精神状态。睡眠品质不好又影响体力,变得更难找到工作,也缺少愿意互动的对象,支持系统便越趋薄弱,约有六成的女性流浪者精神状况不稳定。” 丸山里美观察发现,长期相对稳定的群体性露宿生活会逐渐形成新的社会关系。2000年初,日本东京都的几座公园中都分布着规模不一的“帐篷村共同体”,来到这里“定居”的流浪者因为都是“有过去”的人,而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共同性,他们能够日常互相打招呼,交流露宿生活必需的信息,以及通过建立一定的赠予关系来共同降低露宿生活的物质风险。 然而后来的这些年,这样的“帐篷村”也在急剧缩小,不只日本,全球多国的公共政策中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对流浪者的排斥。直到2021年丸山里美写作《贫困女性在哪里》时,她直言当年书中描绘的那种“在公园创建社区”的露宿者生活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在政府的公告中,流浪人口的比例这些年大幅下降。 尽管露宿生活对女性流浪者而言意味着许多的不确定和危险,但被问及是否想要结束这样的流浪生活时,很多女性流浪者的答案是相当模糊的。书中提到的73岁的顺子在丈夫离世后失去了曾经赖以维生的保障金,无法顺利读写且没有孩子的她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曾被相关的福利机构收容过,但她的生活却几乎重复着某种循环——因情况危急被救助,在多地领取过生活保障,然后再次失踪。起初就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何明明觉得露宿很辛苦,但依然还会选择失踪。 在丸山里美接触到的女性流浪者中,和顺子有相似行为的不在少数。她们总是反复失踪,偶尔会主动回来,有时会被警方找到。她们似乎“很难搞清楚自己的需求,并将需求清晰地传达给周围的人,最终独立实现自己的选择”。不仅如此,当这些女性流浪者在不断讲述碎片化的记忆时,她们的生活史很难被组织成容易理解的叙事,或者说并不符合如今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有“主体性”的个体叙事。 这些都引起了丸山里美对既有研究,甚至是自己无意识中已经带有的研究视角的反思。当作为个体的女性流浪者的生活没有被真正走近时,人们就很难理解女性流浪者或者说底层社会女性群体的真实处境。比如在后来的走访中,丸山发现看似温顺的顺子实际上并不适应与他人同居的集体生活,因为无法处理机构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她宁愿重新露宿也不想回到机构。 在丸山里美看来,这些女性流浪者反复摇摆的抉择中,她感觉到她们身上某种类似“意愿”的东西。“在多项选择间犹豫不决,半是偶然地作出决定,其后又长时间地在失败和他者的关联中继续维持”。 编辑(Edit) 删除(Delete) |

|

|

|
| 版权所有(C), 2002-2025, 卡城华人网中国版 www.calgarychina.ca |
| 版权所有(C), 2002-2025, 卡城华人网中国版 www.calgarychina.ca |